屠呦呦、青蒿素、抗药性、新突破……想必今天很多网友都被这几个关键词刷屏了。
还引发了网上科技类医疗卫生类大V对报道用词不准确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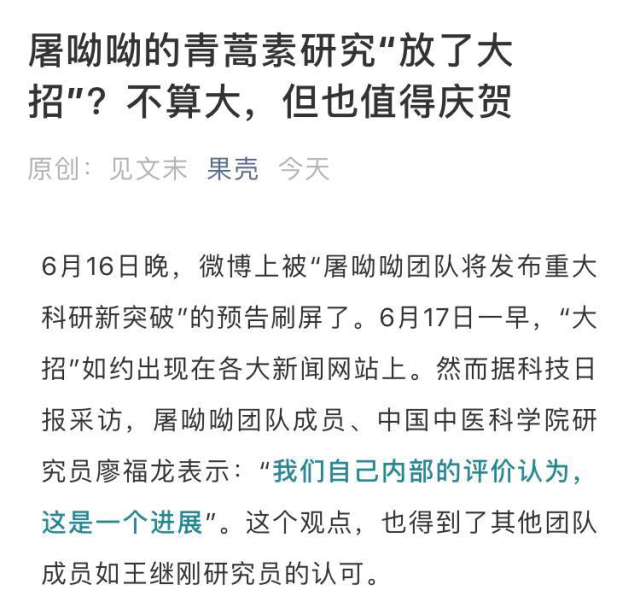
这一研究成果具体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重要?广东与青蒿素之间有哪些故事?有料哥今天就给大家来唠一唠。

⊙你需要了解这些青蒿素知识点
青蒿素联合疗法是世卫组织目前大力推广的一线抗疟疗法,是当前全球抗疟的最重要武器。然而,由于疟原虫对青蒿素类抗疟药物产生抗药性,不少地区疟疾防治情况陷入停滞状态。
屠呦呦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具体是什么样的?有料哥用最简单的语言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研究团队首先在柬埔寨地区发现,有患者在接受青蒿琥酯治疗后,体内寄生虫消除速度减缓了。随后,包括缅甸、泰国、老挝和中国在内的“大湄公河次区域”也发现了“寄生虫清除延迟现象”。

要想破解“青蒿素抗药性”难题,就必须搞清楚青蒿素的作用机理:
患者服用青蒿素后,在人体内仅1-2小时,药物浓度就会下降一半。而目前临床采用的青蒿素联合疗法疗程为三天,也就是说,在整个疗程中,青蒿素真正高效的杀虫窗口只有4-8小时。
这些耐药的疟原虫就充分利用了青蒿素半衰期短的特性。在患者服药后体内药物浓度较高时,它们会狡猾地改变生活周期或暂时进入休眠状态,这样高浓度的药物就无法杀死它们。
同时,疟原虫对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抗疟配方药”,如氯喹、甲氟喹、哌喹等,也可产生明显的抗药性,使得青蒿素联合疗法“失效”。
看到这里,有料哥明白了。其实,这也就是说,可能疟原虫并非是对青蒿素产生了“抗药性”,而是它躲过了青蒿素的查杀。而与此同时,对于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疟原虫会产生抗药性,这样两种药物都会“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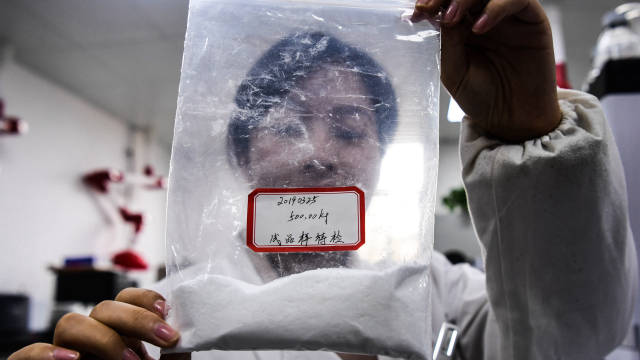
明白了其中的机制,就可以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了。屠呦呦团队提出的应对方案是: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将疗程由三天增至五天或七天;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疗效立竿见影。
为何这一成果这么重要?屠呦呦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青蒿素依然是人类抗疟首选高效药物;而且,青蒿素抗疟药价格低廉,每个疗程仅需几美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更有助于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
⊙团队成员更愿意用“进展”来表述这一成绩
从6月16日发出预告视频到今天新华社报道使用的“放大招”一词,让有料哥很激动。不过,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发出后,也引来了一些批评。其中最主要的矛头是指向其实这一成果并非是最新出炉,而是早就已经在专业期刊发布,而且并非正式的研究论文发布,而更像是一篇综述文章。

屠呦呦团队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标题为《A Temporizing Solution to Artemisinin Resistance》。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王继刚研究员,屠呦呦研究员指导团队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章发表在栏目perspective,在杂志的简介中,该栏目偏向于对公共卫生领域问题发表观点与看法,确实并非正式发表的论文。
时隔两月,青蒿素抗药性研究因为媒体冠之以“放大招”的策划,再次成为热点,让很多圈内人士都感到有些意外。
屠呦呦研究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龙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目前新的治疗方案还没有应用于临床,仍需多方协调,并根据地域不同进行调整,真正落地应用的时间表还不清楚。
“我们自己内部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进展。”廖福龙坦言。团队成员、文章第一作者王继刚也认为,作为科研人员,他们更愿意用“进展”来表述这一成绩。
这项成绩是否真的是“放大招”?有料哥也请教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李国桥教授也是青蒿素的发现者之一。他告诉有料哥,他认为这并不是重大科研突破。
李国桥指出,在实验室条件下,对疟原虫进行培育,可以使之产生低水平的青蒿素抗药性,但这一比率不超过10%。这样的抗药性其实并不会影响临床治疗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临床并不会使用青蒿素单方,使用的均是复方青蒿素,也就是青蒿素联用氯喹、甲氟喹、哌喹等辅助药物,李国桥称之为“配伍药物”。在实际的抗疟治疗中发现的“青蒿素抗药性”,其实是复方青蒿素的辅助性药物产生了抗药性,这一事实已经早被发现,并非是新的突破。他认为,目前复方青蒿素是主流抗疟方式,如果发现效果不好,更换辅助用药即可。
对于7天治疗方案,李国桥并不看好。他表示,其实在1996年,他就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青蒿素单方使用3天,疟原虫会有50%复燃率,使用5天有20%的复燃率,连用7天才能将疟原虫的复燃率降低至10%以内,达到90%以上的治愈率。
但7天方案最大的缺陷是患者的依从性比较差。“在疟疾流行地区,基层的患者难以坚持连续服药7天,导致抗疟治疗效果不好。”因此,2001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确定要使用复方青蒿素,并使用辅助药物来弥补青蒿素单方的不足,这样就可以把疗程缩短到2—3天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抗疟效果。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宋健平长期在非洲抗疟一线,与疟疾作斗争。他对这一成果怎么看?有料哥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
宋健平告诉有料哥,目前,广州中医药大学抗疟团队在非洲国家使用复方青蒿素治疗,效果还是明显的,防治率达90%以上,“在已进行疟疾防治的非洲国家,尚未发现抗药性。”

⊙广东与青蒿素有着难分难舍的故事
广东与青蒿素有着一段特殊故事。故事的主角之一,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一个接力棒式的过程:屠呦呦第一个发现了青蒿提取物有效;罗泽渊第一个从菊科黄花蒿里头拿到了抗疟单体;李国桥第一个临床验证青蒿素有效。”
为了研究对抗疟疾的药物,李国桥两次“以身试药”,更曾写下遗书。

1964年,李国桥就开始从事针灸对抗疟作用的研究。1968年底,李国桥为了检验针灸治疗的效果,李国桥主动叫护士把疟疾病人的血注入他的体内,故意让自己感染并以针灸治疗。但这场试验以失败告终,此后,李国桥加入了中草药组的研究。
1974年秋天,李国桥在治疗一位脑型疟疾孕妇时,尝试使用了青蒿素。幸运的是,患者最终苏醒了。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1982年8月,李国桥等人撰写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从此,青蒿素成为全球抗疟专家的关注焦点。
1981年,李国桥为了验证恶性疟原虫每个裂殖周期引起二次发烧的理论,将疟原虫注射进自己体内,48小时期间不服用任何药物。李国桥在“遗书”中写道,“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需要,请领导和妻子不要责怪试验的执行者。”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仍然记录着当年李国桥和他的同事亲身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
广东与青蒿素还有着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叫做“我在非洲抗疟疾”。
在被称为“月亮之国”的非洲岛国科摩罗,疟疾致死率较高。广东有较好的中医基础,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也在十多年前就致力于青蒿素复方研发。
在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外交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由广州中医药大学与广东新南方青蒿科技公司联合组织的“青蒿素复方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先后于2007年、2012年和2013年在科摩罗所属的莫埃利岛(3.7万人)、昂儒昂岛(32万人)和大科摩罗岛(40万人)实施,超过220万人次参与。
在当地,抗疟团队调整了防蚊灭蚊的防治思路,提出青蒿素复方快速灭源除疟的方法,即通过全民服用青蒿素复方,消灭人群体内的疟原虫,从而消灭疟疾源头。
“说白了,我们就是在与蚊子的寿命赛跑。”一直奔走于世界各地推广青蒿素抗疟的李国桥教授说,如果全民连续两个月服两次药的话,可以让人体内60天没有疟原虫,而蚊子的寿命大约1个月,等到上一批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死去,新一批蚊子即使叮咬了人也不再携带疟原虫,依此,问题迎刃而解。
2014年,科摩罗实现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减少为2142例,比2006年项目实施之前下降98%。
2012年,时任科摩罗总统伊吉利卢在昂儒昂岛“全民治疗”启动仪式上也带头服药。在“全民治疗”后,2014年和2015年,莫埃利岛和昂儒昂岛先后清除了疟疾。
如今,非洲科摩罗的抗疟成功,形成了适合非洲国家的、以复方青蒿素群防群治、全民服药为主的快速清除疟疾“中国方案”。
【记者】黄锦辉 李秀婷 朱晓枫
【统筹】点小羊
【校对】居伟强
链接: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1906/17/c2330996.html?colID=2343&firstColID=2343&appversion=5500&layer=5&share_token=NzEwNWU3MTAtYzJkOS0xMWU3LTgyNjUtNmM5MmJmNDcxMzA4&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date=ODg3NDE5YzYtZWM4ZS00NjQ3LWFlNDgtNzI3ZmU5YTBiZTBm










